投资风险防控之法务定位:法务只审合同吗?
来源:法律安全管理总部 李根 | 发布时间:2020-08-25
摘要:在复杂的投资项目中,传统的法务被动收集边缘信息、被排除在决策和意见的核心圈子之外;风控的法务主动设计交易、以风控的名义推动项目完成。谁的价值更大不需要再赘述了!每一个法务都可以在TA现有的工作职责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冲破别人甚至自己设定的职责边际,逐步把核心价值锁定在根本性的需求上而不是完成根本性需求的载体上!
法务只审合同吗?这看似是一个no-brainer的问题:几乎所有法务,无论职级高低、无论经验深浅,都会义愤填膺的否认、进一步罗列法务除了审理合同之外其他“高大上”的工作!然后可能再默默的“咒骂”一下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对其轻视法务工作的行为嗤之以鼻。
但其他部门的人、法务的直管领导又是怎样看待我们的工作范畴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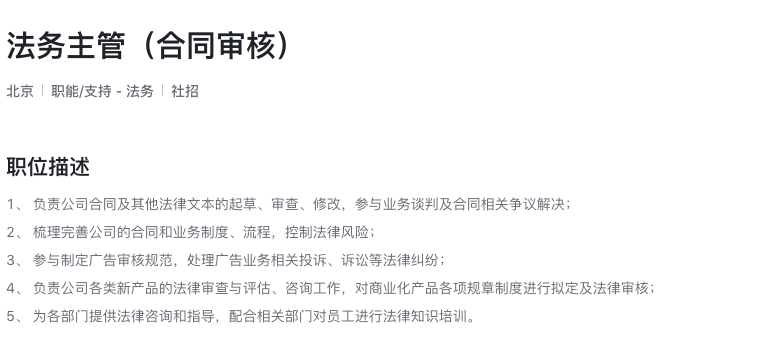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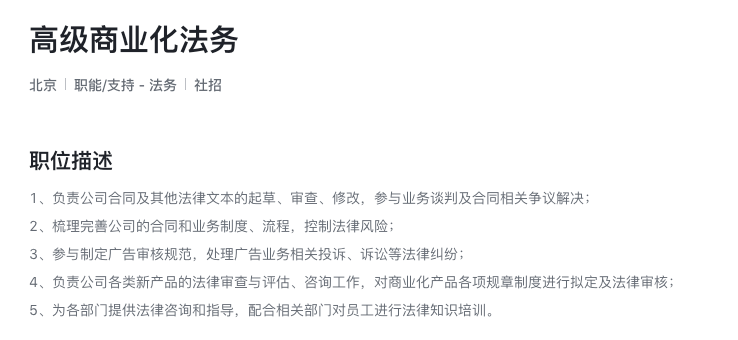
以上是某国内最炙手可热的互联网公司两个法务职位的职位描述,基本符合法务职位职责的普遍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比较初级的法务主管还是比较资深的高级法务,无论是主管合同方向的还是业务法务,其最核心的职责都是和合同相关,并从合同不断再进行延展。所以至少从HR的眼中,我们法务就是审合同的!
如果各位法务同僚不服气,不妨再查看一下自己的会议日程、有多少的跨部门会议是合同相关的讨论?或翻一下邮箱,又有多少比例的邮件的抬头是“XXX协议的修改意见”?
所以无论法务自认为我们的工作多么的丰富多彩,但在中国目前法务市场的大环境下,我们定位的核心就是处理合同,而且我们不断通过努力再持续的强化这一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花一点时间思考两个问题:一、我们的作用价值真的只是处理合同吗?二、我们该用怎样的方式重新定位我们的价值。
说了这么多,本人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刻意贬低合同的价值,而恰恰是要客观的定位合同的价值。根据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4条描述的定义: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我们拆解一下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两个核心信息:第一:民事主体(也就是自然人、企业等)需要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第二:处理这个事项的载体叫做合同,即合同=载体/手段。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结合法务的工作内容,如果我们在处理合同,我们实际上处理的并不是事项本身,而是完成此事项的载体或手段。
我们需要意识到合同并不是完成某一事项唯一或是必须的手段;虽然合同可能是目前为止主流的手段,但谁也无法保证在未来也将保持这一状态。无论是小到一个个体、大到一个企业,很多的事项并不是通过订立合同而完成的。所以合同客观的价值就是处理事项的一种载体,最多是现阶段比较主流的载体而已!
这么说可能比较抽象,我们来做一个横向比较:说人类自古以来都有出行需求,在轮子和马等未被发明或驯化之前,人类是靠人类自己的身体完成这一需求;之后就是利用马车等交通工具;当蒸汽机出现之后马车也被淘汰而换成了火车或汽车;再之后就是飞机、轮船,而实现更远距离的出行我们有太空飞船。随着科技的发展,无法想象又会出现什么新的革命性的交通工具。而合同就是一种交通工具,好比汽车或火车,仅仅是漫长人类出行历史以来某个特定时点的特定用途的交通工具而已。交通工具会有革新、存在替代,存在局限性,但人类出行的需求却不能替代;就像合同也会被替代,但背后的事项或需求很难被替代。所以这就是很多非常“聪明”的公司,尤其是早期的公司,不配置法务人员,但一定会配置财务人员的原因。
所以这时候我们不妨冷静的去想一想,我们是处理一个可能被替代的载体更有价值呢?还是处理一个根本性的需求更有价值呢?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反应比较快的同僚振臂高呼:法务应该决策核心事项!但本人并不十分认同这种观点:核心事项的决策需要考虑的角度非常广,不仅仅局限于法律这一个角度,能力配不上权利是十分危险的!而且处理核心事项或需求不代表一定要决策,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有一个根本性的需求是法务天然而且最胜任来去处理的:风险防控!无论是大到收购公司、小到采购设备,都需要风险防控,人类对于损失的厌恶造成了风险防控是几乎所有需求的必备环节,那么放眼望去,还有谁比一群无时无刻不在研究法律、争议纠纷的法律从业者更适合发现、揭露和预防风险呢?
我们用一个投资案例来说明一个做风险防控的法务和一个单单做合同审核法务的价值区别:
首先说说投资项目的标准流程:1无论投资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投资项目一般遵循惯常的步骤:按照时间顺序包括以下流程:第一、项目筛选阶段:根据投资/收购方需求筛选合适的标的;第二、初步谈判阶段:初步接洽,以获取对方信息,并敲定核心共识、交易架构及下一步尽调和协议签署时间;第三、尽职调查:对标的进行全方位尽职调查;尽职调查可能一次也可能多次完成,可能仅涉及某一方面也可能包括业务、财务、财务等全方面,目的是摸底;第四、签署协议;第五、交接:包括股权、业务、责任等交接和切割工作。
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法务一般参与投资项目是第三步尽职调查及第四步协议阶段,少部分法务可能会涉及到第五步交接阶段;绝大部分情况投资法务参与的范围是尽职调查中的法律部分,主要包括股权的瑕疵、重大合同的法律风险、诉讼争议行政/刑事处罚等,很少同财务务尤其是业务方面的尽调进行沟通,连相互讨论多很少涉及、更别提交叉验证了;在协议的阶段主要是协议的起草、审阅,其中涉及到业务、商务和财务部分一般以标注的方式请各部门进行修改或补充,对于尽调中发现的法律风险,采用协议保护的方式规避,其他部门发现的风险一般不属于法务处理的职责范围。
我们再看一下投资案例,请大家先脑补一下传统投资法务在这个案例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目标公司是一家生物制药公司,拥有一款原料药(API)的生产文号(即生产资质)但并不拥有相应的生产技术(GMP技术);投资方也是一家生物制药公司,拥有这款原料药的生产技术但没有生产资质,且是目标公司的下游公司。为了保证投资方的产品原料的供货稳定性和成本控制,投资方有控制目标公司的需求。
在商务团队在锁定交易对手后设计了两套投资方案:一种方式是全资股权收购,完全控制目标公司;第二种备选方案是收购股权或增资目标公司,完成51%股权控制,以达到控制目标公司目的。
经过初步接洽和全面的尽调,发现这家公司存在四大核心问题:一、股东常年内斗,部分股东想卖、部分不想卖,无法确定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二、股东和管理层,以及管理层之间管理理念不合,造成公司管理十分混乱且不具有持续性;三、经营不善,造成公司经营效率低下,资产利用率很低,且战略发展不明确;四、债务复杂且可能存在大额或有债务。
以上这些风险就给本投资项目造成非常大困难:一来很难确定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利益相关方态度,无法确定股权投资是否可以实现;二来即便可以完成投资,很难承接这个企业的运营:管理层是去是留?去谁留谁?空缺的岗位是否有经营人才可以补位?负债的债务如何处理?以上的这些问题给商务部门设定的两个投资方案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如果就此放弃也是战略上不允许的:上文仅仅提到了目标公司是投资方的上游,但实际上目标公司的产品是投资方产品的最核心原料药唯一来源,是命脉;而且投资方只有这一款产品;并且目标公司也被其他的竞争对手盯上了,所以如果这笔交易做不成,投资方的自身存亡的决定权也将拱手送人。
一个传统意义的投资法务在这个项目中能起到什么作用?首先,不好意思,这位法务可能都无法获知这些风险:以上的这些风险均不在传统法务的尽职调查范围:股东内斗、理念不合、经营混乱属于商务和业务尽调范畴、债务复杂属于业务尽调范畴;而且“本着非法务事项与我无关”的原则,这位法务可能也无法获得这些风险的相关信息。那么既然法务都不了解风险,自然也会被排除在决策或意见成员之外,那么很有可能这个投资项目在没有法务参与的情况下就被毙掉了!那么最后如果投资方真的因为原料药来源被切断而活不下去,那么法务也只能另寻出路了。
那么一个做风控的法务该如何参与到这个项目中而力挽狂澜呢?第一步是理清核心商务诉求:投资方真正想要的是控制原料药的生产/供货,而股权控制只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而且不是唯一手段,通过协议或其他方式也可以实现;第二步是设计交易思路:既然投资方有技术、目标公司有资质,就可以通过投资方授权技术给目标公司委托目标公司生产并独家向投资方供货的方式实现原料药的生产/供货控制,这样可以完美的避开股权投资中的各种风险;第三步是加入风险防控措施:在协议中明确技术授权路径和范围、设置高额的违约金条款、选定有利的争议解决方案,这些都是法务擅长的;同时以监管交易落地执行的名义指派专人,除了负责监督生产,也是为了排查任何违约的风吹草动情况。
以上这一套流程下来,不仅仅交易做成、而且做到了有效的风险防控,使公司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法务在整个过程中并未越权进行任何的决策,仅仅是以“风险”防控的名义帮助企业达成了目标。
所以在这个复杂的投资项目中,传统的法务被动收集边缘信息、被排除在决策和意见的核心圈子之外;风控的法务主动设计交易、以风控的名义推动项目完成。谁的价值更大不需要再赘述了!每一个法务都可以在TA现有的工作职责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冲破别人甚至自己设定的职责边际,逐步把核心价值锁定在根本性的需求上而不是完成根本性需求的载体上!